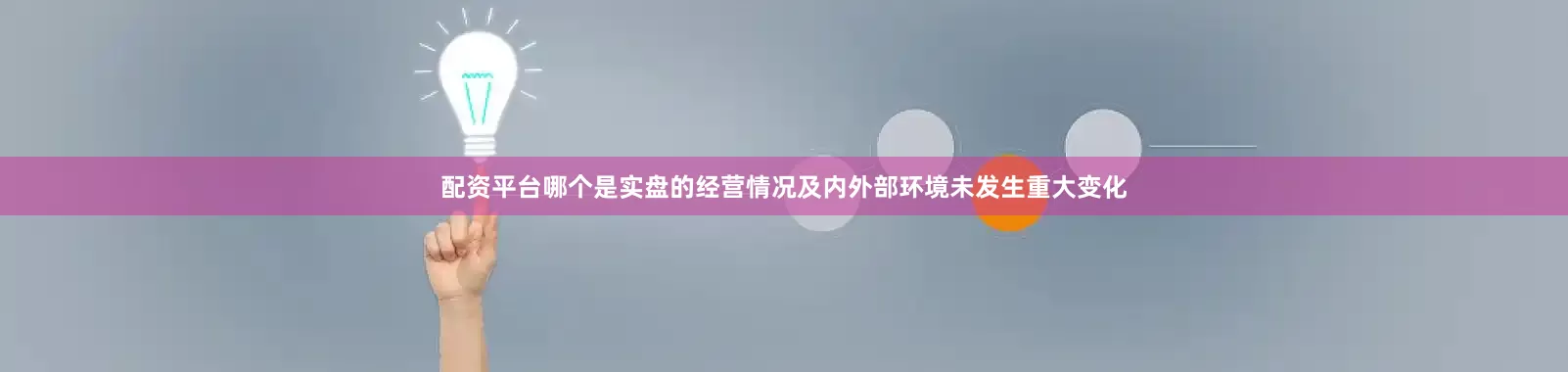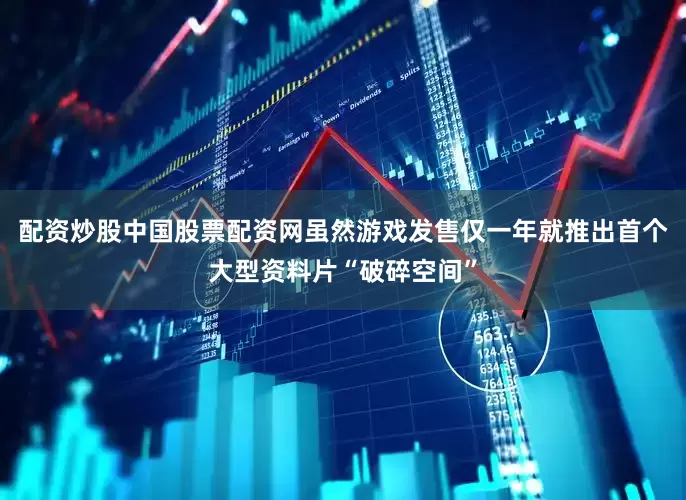很多变化,都是不经意间,等你突然察觉的时候回头一看,才发现已经变了很久,变了很多。跬步成了千里,量变成了质变。
其实这种变化就一直在你身边波澜不惊地发生着,平时压根都没有在意,突然在一个不经意甚至很平常的小切口中,你会猛然咦的一声感觉有所发现,然后再稍微若有所思,瞻前顾后,才发现已经变了太多太多。
比如,我们所在的这栋写字楼内外。
这个小切口,是最近一个上午的停车。
写字楼是高新一期的一栋老写字楼,没有地下车库,仅就地面上绕楼半圈,有大概三四十个车位。这可是一栋30多层的写字楼,自然是车多位极少,停车向来难。
在这栋写字楼上班大概也有七八年了,我在楼下停车的次数屈指可数,大部分时间都是停在较远的一个立体车库,不是我不想停到楼下,而是来了根本找不到空空。别说写字楼下了,就是相邻的路边市政停车位,也都是一空难求。
一般情况下,我如果赶在早上八点前到,基本上都能在楼下找到停车位,如果八点半左右到,运气好的话,踅摸踅摸,在楼下或者路边也能找到个地方,但是如果九点以后,根本想都不要想还有就近停车的地儿。
最近的一个上午,差不多快十点了,我开车去单位,因为想着只是上去查个资料拿个东西,不用待太长时间,就把车开到了写字楼下,心说随便找个地方放着,也就一会,大不了有人打电话下来挪车。
然后,果然随随便便就停下了,不是随便找了个影响交通的地方停着,而是居然还空着好几个车位,我一进来就看到了,“随便”找个车位,没费啥事就把车好好地停下了。

在这之后便对楼下的车位多了些留意,然后经常性地发现,差不多每天,或多或少,都有空着的车位。
二
因为多留了心,便发现了更多的变化。
除了停车不再难,还有就是吃饭也不是那么难场了。
最早在这个区域上班的时候,我也随大流,差不多都是中午十二点左右下楼吃午饭,结果整条街以及与之关联的窄道道无名路上,大大小小的馆子,除了特别不适合老陕胃口或者特别高大上的,其他不管是卖啥的,无不人满为患。能跟陌生人拼座一桌都是运气好,经常性地是要在外面等座。有人可能会说为啥不走远一点,其实走远点也一样,远处的别的写字楼的打工狗们一样也在这段时间踅摸吃饭的地方呢。
我实在不想挤这个热闹,便把下楼吃饭的时间调整为十二点半左右,结果还是好不到哪里去,无非等座的时间短一点。
只好再把时间往后挪,推迟到十二点五十左右,这下确实好多了,起码不用等座了。但这样一来,想饭后午休一会是彻底没戏了。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中午吃饭,不再像打仗一样了。
还是习惯性在十二点五十左右下楼,随便一家馆子,都有不少的空桌。有的里面差不多都没人了,敞亮地很,自在地很。
偶尔下去的早,不管是十二点还是十二点半,随便一家馆子,总能第一时间找到座位。
一家饺子馆,原来只要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去,哪怕大太阳呢,外面的桌子都坐满了人。如今,啥时候去都有空位,除非特别舒服的天气,外面压根就没人坐。原来,自助的饺子汤经常性是空壶,现在,配上了免费的稀饭和小菜,哪怕到一点多去,都还很充足。

正街上,背街上,都有曾经火爆的馆子关了门,玻璃门上贴着的转让招租启事,经历着一天又一天的风吹日晒和雨打。
三
写字楼外部的变化,大概是与写字楼里面的变化是相关联的。
就拿吃饭来说吧,曾经,公司的几个小女生每到中午快下班的时候,就叽叽喳喳地说谁家的饭好吃,相约着同去,如同快乐的小鸟。
这几年,这样的声音是越来越少了,取而代之的,是悄悄地从包里拿出家里带的饭,轻轻地放进微波炉中。原本的叽叽喳喳,变成了此起彼伏的微波炉的叮叮声。
电梯也好坐的多了。
写字楼的电梯,一般都会有几个高峰段。
一个是上午八点半到九点半,这时候,白领子蓝领子的打工狗们都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上班了。这一个来小时,这栋写字楼三部电梯的电梯口,排队的人可以沿着走道逶迤拐三个弯,一直排到大厅。
中午则是上下楼都难场,吃完饭或者买了饭的,加上蓝衣服黄衣服的送外卖的,照例从电梯口开始排长队等上楼。下楼的尤其是中间楼层的,基本上是等不到下行的电梯开门的——因为里面早已满载了,就算电梯停下门开了,往里面一看,乌泱泱一片根本再容不下一双脚。无奈,只好先按上楼键跟着上到顶层再下来。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几个高峰段的电梯,不那么难坐了。

上午高峰段照例还是要排队,但在九点以后基本上就不用排了,而且,队伍也不再那么长,差不多一个队也就十来个人,一趟电梯就能全解决。
中午的变化也很明显,甚少在下行的时候等不到能开门的电梯,下到一楼也许还会遇到上楼的再排队,但电梯一到走廊立马就空了。
四
这一切的变化,都在印证着这栋楼里面的人,明显比以前少多了。或许,周边的写字楼,也都是相同的情况。
肉耳可听的,就是整栋楼安静了很多。
肉眼可见的,就是整栋楼空了很多。
就拿我们这一层来说,我们七八年前刚搬来的时候,整层楼都是满满当当的,我们其实也是接了一个原本就在这里的老摊子做了业务的调整,不然,根本就没有插脚的机会。
大概就是疫情期间,一层楼开始出现了空房子,那时候空的还不算太久,过上两三个月便有新的公司搬进去。然而,情况却没有变成疫情前灯火通明热火朝天的样子,相反,同一间房子,门口牌子的变换频率越来越高,中间的空档期也越来越长。
直至从一空再空变成了一直空。
直至去年年底,上千平米八个门头的整层楼,竟然就只剩下了我们一家。其他的,都空了,都锁上了。曾经灯火通明的一层楼,变成了黑咕隆咚静悄悄。曾经在这些门头里热火朝天地打拼的那些小公司们,也不知道是搬到了别处,还是坚持不下去彻底关门了。

别以为我们还开着门就能好到哪里去!还好最近一笔银行的贷款下来了,不然,我们也早被越积越多的欠款(别人欠我们的),拖得只能关门了。
这就是一栋写字楼的内外变化。在这样的变化中,我每天还开着车,穿着衬衣皮鞋,人模狗样地继续在这里出出进进。只有我自己,才知道自己心里是多么的恓惶和惶恐。
十大权威安全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